且讓我為你述說一段故事。當這故事到了尾聲,我們能否依然相愛相親?
這是一段漫長的故事,因為它涉及所有對你我至關重要的事物:我們的價值觀、原則、認同的根源、社群的基底,關於你我之間的合作與對抗,關於譴責與被譴責的兩方,而且醒時所見往往未必如同入眠之前。
我們能依據什麼定位自己?我們希望怎麼生活?你我彼此如何互處?過去我們是怎麼做到的?未來又有何可能?這些都是道德的問題,而我要述說的故事,即是一段道德的歷史。道德,它聽來似乎就等於禁止與強制、限制與犧牲,道德是宗教法庭,是懺悔與良心不安,是貞潔與教義問答:無趣,幽閉,而且總愛說教,好為人師。
這些印象倒也沒有錯,只是不太完整,還有補充的必要。我要述說的故事將回溯人類根本的道德演變,從東非地區尚未成為現代人的遠古祖先,一直到現今世界各大都會中,在網路上激烈上演的種種衝突――關於身分認同、不平等、壓迫,以及對當前局勢的解釋權。這個故事將講述我們的社會如何在時代更迭中發生變化,而新的制度、技術、知識體系和經濟形式又是如何與我們的價值觀及規範同步發展,而且,這些變化全都不只有單一面向:生活在一個群體當中的人會排斥外人;了解規約的人會想控制規約;予人信賴的人會讓自己仰賴他人;創造財富者同時也創造出不平等與剝削;想要和平的人有時也必須起而戰鬥。
每一次的變化都有其辯證,每個良善、美好的發展也都有其艱難、陰暗、冷酷的一面;所有的進步都有其代價。早期的演化讓你我懂得了合作,卻也敵視「非我族類」的他者――說出「我們」的人,也會同時說出「他們」。刑罰的發展馴化了你我,讓我們變得相處和睦,卻也讓我們具備強大的懲罰本能,藉此監督你我依循的規範;文化和學習讓我們有了從他人身上習得的新知識與新能力,卻也讓我們因而需要仰賴「他人」。不平等與統治的出現,為人類帶來了規模前所未有的財富,以及程度前所未見的階級和壓迫。現代性解放了個人,個人則藉著知識與科技控制了大自然;對於這個此刻你我在當中已無家可歸的世界,我們早已除魅,再無幻想,而且還創造出了生成殖民主義和奴役制度的條件。二十世紀原本希望借助全球機構,創造出一個人人皆能享有同等道德地位的和平社會,然而帶來的卻是人類歷史上最駭人的罪行,並將我們推向生態崩潰的邊緣。近來,我們致力於根絕專斷和歧視、種族主義及性別歧視,以及恐同和排外的遺毒。這樣的企圖將能得到回報,但我們也將為此付出某些代價。
我們的道德如同一張刮去前文、重複寫上內容的羊皮紙,無以辨識又難以解讀。然而道德是什麼?我們如何定義道德?最好的定義方式,就是完全不去定義,因為「唯有不具歷史的東西才可定義」。然而我們的道德確實有其歷史,而且那歷史太過龐雜、笨重,不是我們安坐書房中所想出的空泛公式能夠形容。道德難以定義,但那並不表示我們無法清楚說明道德是什麼。它只是無法以三言兩語說明。
道德的歷史不是道德哲學的歷史。長久以來,人類都在思考自己的價值觀,但直到最近才將想法寫下。《漢摩拉比法典》、《十誡》、《登山寶訓》、康德的「定言令式」,以及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的「無知之幕」,這些都在我將述說的故事中占有一席之地,然而也都是相對次要的角色。這是關於我們的價值觀、規範、制度和實踐的故事。道德不在我們的腦袋裡,而是在你我的城市和堤壩、律法及習俗、節慶和戰爭當中。
我將講述的故事,意在幫助我們理解現下。當前的現代社會正處於道德壓力之下,它需要調和自身存續的可能性和最令人不安的真相。如何才能重繪出你我正置身其中的道德基礎架構,進而完整揭示它的全貌?我們現今見到的這種兩極分化、無可調和的狀況,究竟從何而起?文化身分與社會不平等之間的關聯為何?這些要素最終會連結起來,形成對當前道德危機的診斷。我將在本書中講述人類道德的歷史,而我提出的診斷,也正是源於這段歷史。要理解當下,就必須回顧過往。
簡言之:道德的演進讓我們有了合作的能力,卻也將我們的道德傾向局限在會被我們歸為「我們」的群體當中(第一章,五百萬年)。
外部環境的持續變化提高了合作的必要,而人唯有共同生活在規模不斷增大的群體當中,才能滿足這個需求。懲罰的實踐讓我們一方面具備了必要的個人自制及社會的和睦相處,另一方面也產生出一種心態,讓我們以最高的警覺度,監看你我是否遵循著群體的規範(第二章,五十萬年)。
基因及文化的共同演化讓我們成為仰賴向他人學習的生物,藉此有效地吸收眾多積累而成的資訊和技能等文化資本。同時,我們也必須能夠決定要向誰學習――也就是要信任誰、相信誰,而這種信任感的發展,要以共同的價值觀為中介(第三章,五萬年)。
人類這個具有合作性、懲罰性和適應性的物種,最終成功建立起規模愈來愈大的社會,而這些社會在其自身成員數量激增的壓力下,面臨隨時崩解的風險。於是,區別嚴格的階級組織形式開始取代最初的平等主義,將人類社會分裂成了兩方,一方是社會經濟菁英階級,另一方則是在政治和物質條件上居於弱勢的大多數人。社會不平等現象日益加劇,我們對於不平等的厭惡感也與日俱增(第四章,五千年)。
道德的歷史遲早會產生一種文化構造,以在個人之間自動形成的合作關係,取代固有的親族關係和階級制度,做為社會結構的新原則。這個社會進化的新階段釋放出前所未有的力量,推動經濟成長、科學進步與政治解放,形成如今我們生活於其中的現代社會(第五章,五百年)。
與此同時,世人對於社會不公的心理反感,和以個人自由為基礎的社會結構所帶來的經濟利益,這兩者之間的矛盾也日益加劇。隨著物質益發豐足,世人要求實現人人平等之承諾的呼聲也漸趨高漲:弱勢少數群體的社會政治地位於是成為道德的優先考量(第六章,五十年)。
這個問題無法如願地快速解決,這正是當前情勢的特點,人類道德歷史中的主要元素彼此結合、交互影響,形成了一種有毒的混合物:我們充滿道德色彩的群體心理,造成你我容易受到社會分化的影響。即便是最近期的社會不平等也難以克服,這就讓世人對所有未能以必要的同等熱情為共同志業而奮鬥的人有所懷疑。這也就加劇了社會對於「我們」與「他們」的分化,讓一般人更容易受假訊息影響,因為我們愈來愈仰賴道德歸屬的信號,好藉此決定要相信誰。
如今,我們的懲罰心理開始更為敏感地審視自己群體成員身分的象徵標誌,並對未遵循當前規範的行為施以愈來愈過度的制裁。當前這種左派與右派之分的身分衝突,正是這種演變動力所導致的結果(第七章,五年)。然而結局未必非得如此。因為你我政治意見的歧異,絕大多數都不過是表面且膚淺的,存在那表象底下的,實為眾人共有、在我心中根深柢固的普世道德價值觀,而這些價值觀能夠成為我們重新相互理解的基礎(終章)。
我說過:這是一段漫長的故事。這則故事始自久遠之前,終點則在未來。故事的節奏會益發緊湊與激烈:第一章到第二章講述的時間橫跨數百萬年,而最終三章合計不過數百年。但請勿依字面看待我所採用的時間劃分,我在文中描述的進展,許多都是相互重疊,或是沒有明定時間順序的。這段敘事所依據的時間劃分方式,應理解為大致的範圍,是為了強調重點,並提供一個概述的輪廓。
原作:Moral. Die Erfindung von Gut und Böse
作者:漢諾.紹爾(Hanno Sauer)
譯者:林家任
https://bookzone.cwgv.com.tw/article/34063?utm_source=line&utm_medium=social&utm_content=post_0730&utm_campaign=bz_gb&fbclid=IwY2xjawMxfQdleHRuA2FlbQIxMABicmlkETFBMnZFa3Z2NVBvbDk4VmpFAR7Y5FoYs8l2BZ_bwjx6ofSS0RPJTZedLsFZFTWDd0xvIBpfxSovstOBKkNBJA_aem_uzc9JzCxmnUPtOX4Y4M1Dg


.jpg)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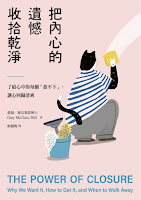






.jpg)



.jpg)
.jpg)










